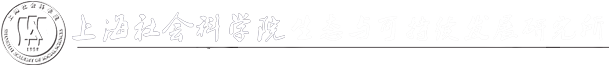作为首次列入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论坛讨论主题的“能源可持续发展与气候变化”,不仅体现了第三届世界中国学论坛的主旨“和衷共济,:中国与世界共存之道”,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是拓展了世界中国学的研究领域,给予了中国学更丰富的内涵,“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一个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的重要话题。 国内外的学者对于能源问题和气候变化的紧迫性,都没有异议。美国《城市技术杂志》的主编Richard Hanley,强调了城市的能源问题,认为能源的可持续性问题,也是城市的可持续性问题,城市的发展不仅要考虑到经济发展,也要考虑到社会整体发展的质量,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如何实现城市的可持续性发展,实现能源的可持续发展。 但是城市在能源问题和气候变化中的责任也是不可回避的,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的胡秀莲研究员,指出根据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07年1月29日―2月1日发布的第四次评估报告,气候变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而人类的活动又是主要的原因,尤其是城市化的推进。 但是面对气候变化和能源问题,我们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跟以往很多研究不同的是,这次论坛上专家学者们不仅是从交通、建筑等具体部门,特别是从第二产业的部门入手讨论能耗与节能减排问题,更多的专家学者开始更多地强调消费和第三产业的能耗问题。上海人大财经委俞国生副主任委员在分析上海节能减排的目标、形势及任务的时候指出,以上海为例,节能减排的任务的实现不仅是要提高能源产业的技术水平,更重要的是要形成一种理性的、绿色的、科学的、健康的消费观念,而培养这种观念应该从中小学开始,从小推动节能减排,形成节能减排的意识。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玉歆更加明确的指出:生产领域的减排潜力是有限,节能减排要改变一手硬一手软(生产硬、消费软)的局面,要把节能减排的工作向消费等领域拓展,做到两手都要硬。认为消费侧节能亟待加强:,要注重消费引导,改变高耗能的生活方式,大力遏制政府搞排场,倡导物质生活简朴、精神生活丰富的消费理念。他还特别指出了目前很多政策的不足,比如认为在中国大力发展私家轿车显然是不符合国情的,另外长期计划生育政策的节育措施其实对于节能也是不利的。此外,他也指出了缩小贫富差距,对于节能减排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而对于这种出路的可行性,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反而更具有一定的后发优势,消费者的消费没有完全成形,更容易被引导。 另外一些学者则从各自不同的领域和部门上来思考这一问题。在交通方面,多伦多城市可持续交通中心前主任,OECD前能源环境分析师Richard Gilbert认为电力交通将是城市交通的出路。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的许光清博士则认为要降低交通的能耗,除了要降低汽车单车的能耗之外,这与汽车行业的技术选择有关,但汽车的燃油消耗还与汽车的保有量、已有汽车的行使公里数、城市的交通道路状况以及驾驶员的驾驶技术等很多因素有关,而这些与消费者的消费习惯、燃料种类、汽车的价格等有很大关系,可以通过政策的引导改变。而上海的赵国通认为自行车是最好的交通方式,并批评了广州东莞等地不允许电动车进入市区的做法,并对上海汽车牌照拍卖制度表示了肯定。建筑方面,国家发改委的刘强博士,在指出了我们国家建筑节能领域存在的建筑节能标准、建筑供热收费机制、缺少相应有效可行的法律制度以及缺少市场激励机制等主要问题,加上分析了国外的很多建筑节能经验之后,指出我国建筑节能领域虽然已经出台了很多的标准和政策,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在实施和落实方面还有很多机制和体制上的问题;在激励问题上,基于市场的激励机制也比较少,还主要是依靠政府行政命令的方式。 专家还指出了技术是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的胡秀莲研究员和国际能源署的Ingrid Barnsley认为节能减排的技术是很关键的一点,也承认技术投资会给经济带来一定的压力,但是认为这种影响是很小的,节能技术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并不大,有必要坚持下去,并且强调了政府在关键技术研发方面的作用应该进一步加强。但是在学习国外节能减排的技术问题上,更多的专家并没有向原来那样强调引进技术,而是更多地认为发达国家发展的道路始终是能源密集型的,至今仍然如此,我们不能走发达国家的生产和消费的老路,反而特别要谨防陷入在引进西方所谓“先进”技术的时候,实际是用西方传统高碳技术建设所带来的更深的技术锁定,不能像工业化国家那样深陷于石油能源技术-经济系统的“碳锁定” 之中。CDM(清洁发展机制)实施中出现的轻环境效益,实际重经济效益现象。也有专家还指出我国目前采用一些不成熟的减排节能技术的成本会很高,引进这些技术的意义不大,目前发展还是第一位的,因此中国不应该在2020之前承诺全球减排的任务。而另外一些学者还是强调了西方国家的很多经验值得学习,尤其是在关键技术和经验上,比如在节能审计制度以及许多节能技术等。